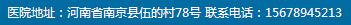当前位置:尿毒症性脑病 > 尿毒症性脑病治疗 > 中共党史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
中共党史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人们一般称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年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从而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欲罢不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从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重要举措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在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发生,华国锋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依照当时面临的情势,无论谁掌舵都需要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力。而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一、“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中国改革何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笔者要说的是,改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但改革的因子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伏下了。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权争,“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年“九一三”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年清明节前后,被称之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背后却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全程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后与贫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其中不少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不止是年轻人,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胡耀邦说:“从年到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改造“旧政府”,但治理国家别无选择,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操办,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些人。林彪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然而,这批人不可能如毛泽东所愿接受“文化大革命”路线,来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泽东很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文化大革命”聚集了否定其自身的力量。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在当时形势允许的限度内纠错“文化大革命”、扭转颓势的一次努力。“文化大革命”也造成一种机会,使各级领导人更加接近底层,直面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或许有利于他们思想上的解放。这一道理如同年中央常委和各地领导人下乡目睹农村的惨状,推动了当年的政策调整一样。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摆脱“文化大革命”噩梦这一点看,多数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为改革准备了干部。“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都伤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而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也改变了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年和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一讨论的开展。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即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年和年期间,部分职工工资的调整、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恢复,都体现了这种思路。有些经济学家的思考,已涉及整个计划体制。例如,薛暮桥年4月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信,就提出研究计划管理体制问题。6月,他还通过对江苏和北京的调查,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现在管理体制根本缺点是,不管是条条管,还是块块管,都是按行政系统管,既割断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割断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条块分割体制的典型弊端是:两个企业能商量解决的问题必须层层上报,由上级领导机关协商解决;一天能办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几个月。他举例说:常州东风印染厂的灯芯绒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为增加生产,需要多进口染料,而因为没有外汇,需要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银行完全同意,但必须层层上报到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打了十几个图章才办完手续,而增加染料进口又要外贸部批准,又得层层上报打了八个图章。办完两项手续,共花了8个月时间,如果准许该厂直接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购买染料,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他还看到:江苏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业,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又不如社队工业。因为地方工业留利比例(60%)超过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而社队工业的留利比例(80%)又超过地方工业。因此,他认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而且要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拨乱反正不止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向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正如于光远所说:“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或者说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但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个是人的政治解放,全面平反历史错案,解决各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个是人的思想解放,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为前导,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推动的。二、改革的经济动因“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年2月12日,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透露:几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两年停滞不前,年只增长0.6%,钢产量倒退5年,不少重点工程形不成生产能力,财政连续3年出现赤字,年财政收入只有亿元,相当于年的水平。据估计,“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也是正式报告中首次出现“崩溃边缘”的说法。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的判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总体上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例如,中国问题学者哈里·哈丁说:“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萧条与饥荒,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在年至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超过了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中国在年毛泽东去世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毛以后的改革却不应被视作是当时中国状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有相似看法的还有鲍大可、莫里斯·迈斯纳等。国内学者陈东林也不同意“崩溃边缘”的说法。他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是发展的。年至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尽管不少人对这样的统计数据存有疑问,笔者仍愿相信“文化大革命”后公布的数据大体准确,“崩溃边缘”的说法太过政治化了。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严重经济困局的事实。这一事实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有关资料统计,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例如,在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队在40元以下。这也意味着,在安徽省万农村人口中,有万以上的人是吃不饱肚子的。农民的贫穷不只是在少数地区。在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来自西北地区的负责人发言说:“西北黄土高原,人口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年前后,北京和各地出现持续不断的上访和闹事风潮,其诉求除了政治平反,就是各类民生问题。例如,在住房问题上,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年还少0.9平方米。根据对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万户,占35.8%。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两平米的,有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成人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有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这一时期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中国长期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子,与之相配套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自5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年到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个。这个成就不应被忽视。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以勉强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治上的松动释放出巨大的民生压力,依靠政治动员强制推行一种发展模式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这条路很难继续走下去。国营企业效益日趋下降,同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年至年间为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年、年两年为负增长,出现了自“大跃进”以来第二个财政困难时期。从财政角度看,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也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三、农村政策悄然转向农业发展滞后是决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