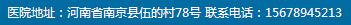当前位置:淤泥 > 淤泥资源 > 母亲短暂的一生7熬夜 >
母亲短暂的一生7熬夜
长篇回忆录《母亲短暂的一生》之7熬夜
吃过晚饭,父亲坐在门口,和来串门的邻居闲呱啦。(有时是直接躺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母亲洗涮完锅碗瓢盆,安顿好几个妹妹睡下,扛起撅头,对父亲和邻居说:“你们在这玩。我去菜园。那片地都干了,天天忙的也没空挖。再不挖,就挖不动了。”
邻居说:“你一会儿都不拾闲儿,干活儿累一天了不歇歇,还摸黑去挖菜园。不要命了。”
父亲说:“她见天瞎慌张。”
母亲笑着说:“你不干,我再不慌张,一家几个嘴,青菜都供不上吃”。
别人家挖菜园这样出力活儿,都是男人一早一晚抽空干。父亲一向不屑于干农活,母亲也心疼他的身单力薄,就从不主动叫他干。
母亲喊上我,去给她做伴。
虽然菜园就在屋后边,毕竟村头空旷,风吹庄家呼呼响,远近有很多老坟土堆,树形摇曳,影影绰绰,她一个人悚得慌吧。就叫我坐在园埂上,一边挖地,一边没话找话哄着我跟我说话,怕我睡着了,或跑回家。
(照说,我哥比我大,更能为她壮胆。但母亲从来不舍得叫他干任何活计。对于那个唯一的儿子,香火的继承者,母亲把他当宝贝养,不愿让他吃丁点苦,不愿委屈他半点。除了回来吃饭,我哥基本也是不回这个无立足之地窄小的屋子,常驻于堂叔那)
明亮的月亮挂在天上,有许多的星星一闪一闪,像一个一个精灵眨着眼。
月光照亮了菜园,如白昼一样。母亲身体前倾,双手轮着撅头把,一下一下往下刨,那影子,叫我想起,课本里愚公移山的故事,想起砍月桂的吴刚。
这个时候,很多人家的母亲,都是坐在家里享天伦之乐,或坐在门口和邻居闲聊天,消解干一天农活的乏。
可是母亲,却还要顶起家里的半边天,加班大汗淋漓地挖菜园。这都是因为她摊上一个不愿干农活的丈夫,一个她眼里的“文化人”,她崇拜的父亲。
母亲就是一个女愚公,女吴刚,挖地不止,干活不止,我都不知道,她高却瘦的身躯里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力量,哪来那么一股干起活来乐此不疲的精神头儿。
不一会儿,母亲就挖热了,只见她脱了外面的罩衫,只剩里面的圆领衫。
夜晚凉风习习,我都觉有丝丝凉意,想回家钻被窝睡觉了,母亲还穿那么薄,我真怕她闪了汗感冒了。可是她一点儿不当回事,说:我热得很,剩下这点儿挖完就穿上回家。
她站着歇歇的空挡,可能看到我歪在园埂上,无精打采想瞌睡,就哄我:“一会儿就挖完了,你再坚持一下下。我给你哼个歌吧?”
不等我应声,她就手拄撅头把,轻声唱:棠梨子树,棠又棠,棠梨子树上盖瓦房。三间瓦房没盖起,婆婆妈妈来送礼。大姑送的金簪子,二姑送的银簪子,三姑送的麦签子。七碟八碗端上桌,哥嫂招呼要入座。大姑坐在上席上,二姑坐在上席旁。兄嫂指着三姑说,你就坐在下席上……
十岁的我,从平时家里来客人让座,已经知道下席和上席的区别,可是还不懂得人情世故的我有个问号:“都是妹妹,为啥三姑要坐在下席上?”
母亲笑:“三姑送个麦草编的签子,最不值钱,她哥嫂看不起她呀。”
从此以后,我就记住了这个儿歌似的说唱,至今不忘。
等母亲挖完菜园领着我回家,屋里已经黑灯瞎火,父亲和几个妹妹早睡熟了,在堂叔家借宿的兄长,估计也早进入梦乡了。
母亲还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那年,公社正倡导办扫盲班,由各大队办的学校里抽出老师,各生产队轮流上课,一星期上一晚上课。
老师来开动员会的时候,好多妇女都不愿意,说:
“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吃罢晚饭好不容易闲下来歇歇,又搞啥扫盲班,拖儿带女的哪有那时间去学?”
“反正是修理地球的老杂皮,都半老不少了,认得几个字,又有啥用?”
……
很多人都没有积极性,都觉得是搞着玩净瞎耽误功夫。
但母亲却欣然接受,积极报名。
也许是耳濡目染,经常看见父亲捧着一本厚书,看得有滋有味,常常还自己发出笑声,母亲一定好奇,书里都写了啥,这么神奇,叫他那样入迷,天阴下雨不出工时,能看一天都不嫌腻。
到了扫盲班有课那日,吃过晚饭,母亲会拉着我一起去。她怕老师提问她,她记不住字的读音现眼,叫我到时现教她。
虽然父亲自己钟情于读书,但对母亲上扫盲班,并不理会,不支持,也不反对,也不帮助指导她。
有时临睡前,母亲一边怀抱小妹妹,一边见缝插针拿起书本,让父亲叫她认字。
父亲就不耐烦的说:“你那记性,说一百遍你也记不住,你自己看去。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生来就是干活的命”眼睛不离书本继续看自己的书。
母亲也不恼,还是很有兴致的,饶有兴味喊过我来,指着她不认识的字,问,这个念啥,那个念啥。
比如我说这个是tian田,她就也跟着读一遍,还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是哩,老师教过这个字,叫田。我老是记不住。我不会拼音,记不住咋拼。”
看得出,她很想学识字,有很大的热情。小小的我自然好为人师,逮着机会,也愿意教她。可是学一会儿,她就哈欠连天,说:明个再学,瞌睡来了。说着,放下书本,没两分钟,就睡着了。
母亲太累了。她没有可以拿来学习认字的时间。她的一切时间,都是要围绕父亲,和我们兄妹五个,和这个家,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余下给她自己的时间,就少得可怜了。
这个扫盲班因为学校老师的不积极,也没有办多久,母亲的一本课本,连三分之一都没学完。而母亲学完的这三分之一,估计她一半都没记住。所以她还是一个读不了一页书的文盲,也所以,她特别的看中,爱学习的人,也特别重视我们兄妹的上学读书。
秋收冬藏后,天寒地冻,农活儿少了,母亲是不是能闲一点呢?
我们当地有句俗话:眼里有活的人,处处是活儿。眼里没活儿的人,房倒屋塌,他也说砸不住他一个儿。
母亲,无论家里家外,她永远是那个眼里有活的人,所以永远手里都有活干。
那些年,正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热火朝天的时候。
每到冬季,大队生产队,就组织男女社员,挖水渠,清水塘淤泥。
上冻的冻土,坚硬无比,撅头刨上去,只留下白色的印子,要三番五次地刨,才能撅起一块大坷垃。
那时又没有钱买手套,刺骨的寒风中,个个都裸口着双手,几乎所有参与修渠大会战的男女社员,手掌虎口都被冻了好多血口子。
母亲白天挖土挑土修渠清淤,回到家,做饭洗刷把一家七口肚子填饱,晚上还要坐下来,做一件很费功夫的事:纺线。
母亲吃的许多苦,都源于,她没有双亲,没有公婆。
但凡像别人那样,有个公婆帮衬着哄孩子做饭,有个妈帮着纺线给孩子做鞋,除去这些非常耗精力、时间的活计,母亲也能轻松一些,不至于一年到头,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没有一次,吃过晚饭不熬夜做活。
那时做鞋纳鞋底,缝衣服,所用的线,都靠自给。生产队分的棉花,拿到集上用弹花机弹弹,去掉棉籽,就是“皮棉”。
皮棉拿回家,摊到桌上,一层层掀起,垫上一张从生产队长那里寻来的报纸(起不沾作用),铺成一尺多长的方块。高粱秸秆顶端的细处,截一尺长的一段,然后放在薄薄的皮棉上,两手在两端,水平地轻轻地往前卷,卷成一个空心的“棉条”。
一次不能做的太多,不然一时纺不完,棉条挤压在一起,就不容易“出线”。
然后用一节“引线”,沾点唾沫,捻在棉条的一头做牵引,缠绕在锭子上。人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右手慢慢摇动纺车的把柄,左手五指巧妙的配合,轻轻夹住棉条,胳膊均速的往后延展扬起,眼睛时刻盯住棉条出线的粗细,随时调整手指捏棉条的力度。
线抽到左手臂延伸最长处,就可以反摇纺车的把柄,把线送到锭子上一圈一圈缠起,直到锭子被棉线缠绕的中间凸起,两头细的一个大线穗子。
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很耗费功夫、且很伤胳膊累眼睛的活计。又是那时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一个活计。
很多人家,这个活都是由六十岁以上,不再下地挣工分在家看孩子的老妈妈做的。纺线几乎贯穿整个儿冬季。因为一晚上加班两个小时。可能也纺不了几个线穗。
可是作为孤儿的母亲,没有妈也没有婆,甚至没有一个近亲属,没有人肯耗时费力帮她纺线。
于是她只有,用父亲比葫芦画瓢做的简易纺车,自己利用晚上时间,一天纺一点。
零下几度的屋里,寒气逼人。买不起煤,又没有多余的柴禾烤火,母亲穿着单薄的棉袄坐在那里纺线,脚一会儿就冻麻冻疼了,她就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用双手搓搓腿,搓搓脚,坐下,接着纺线。
父亲和妹妹们早入睡了。
屋里没有钟表,不知道几点了。外面时不时叫嚷的狗也不吠了。庄上一点儿人声走路的动静都听不见了。好像整个庄子的人和树,都睡着了。
温度更低了,更冷了。
可是昏黄的电灯下,母亲的手还在一伸一缩地纺着,纺着。
(感谢您的阅读!敬请